简论彝族宗教神话中的原始死亡观
牛军 | 云南大学中文系
摘要:彝族宗教神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始死亡观 , 为死亡哲学的源头提供了佐证 , 其内涵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三个方面 : (一 ) 其基本内容是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 ; (二 ) 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 (三 ) 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
关键词:彝族原始死亡观;宗教神话;死亡哲学;
人类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之日起, 就开始面对同类的死亡问题, 他们不得不思考“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真的会死吗?”“人为什么会死?”“一个人会死, 但他所属的群体都会死吗?”诚然, 原始人类尚不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 然而他们却以别的形式如原始宗教活动、原始神话、丧葬仪式乃至原始文学艺术的形式, 把问题提出来。而在这些方面保留原始氛围较浓重的民族有云南的纳西族、彝族等, 特别是彝族已将人的生死问题摆在了突出的地位上进行思考。
彝族对死亡问题的思考虽然未能达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和海德格尔那样的理论高度, 但他们的一些观念却反映了人类孩童时期的死亡意识。人类确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这就是寻根的欲望。文化越是发展, 社会越是进步, 人类的寻根意识就越是强烈, 越是自觉, 特别是对人类死亡问题的审视更是如此。死亡哲学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离开了古人对死亡问题的幼稚见解, 离开了人类对死亡认识的点滴进步, 当代死亡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可贵的是, 彝族的原始死亡观为当今一泻千里的死亡哲学注入了涓涓细流, 为死亡哲学的“源头”提供了佐证。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 人类尚不能对死亡作哲学的思考, 甚至不能用人的眼光和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 这就使人类的原始死亡观普遍采取非自然的宗教神话形式, 也就是说死亡问题始终是同原始宗教神话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作为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始死亡观的最根本特征——是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人论》的作者恩斯特·卡西尔曾经强调神话是关于不死的信仰。在他看来, 宗教神话关心的, 与其说是死亡, 毋宁说是不死。他指出, 那种认为人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终有一死的, 这与神话思维和原始宗教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某种意义上, 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①
就此, 我们试分析彝族的宗教神话表现出来的、以否定为特征的原始死亡观之基本内容:
一、原始死亡观的一项基本内容 是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 不可避免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整个神话可以解释为人类对于死亡的顽强否定。死亡历来是困扰人类的最大恐怖。即使是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类对死神仍是无可奈何。因而在彝族中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要享受生的乐趣, 就必须尽死的义务。然而, 在彝族的神话中却坚持死亡不是必然的, 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造成的结果。
在我国《山海经》中不仅记载了许多不死之人, 还记载了许多不死山、不死之国, 如:“不死民在其东, 其为人黑色。寿, 不死。一曰在穿胸国东”。 (《海外南经》) “流沙之东, 黑水之间, 有山名不死之山。” (《海内经》) “有不死之国, 阿姓, 甘木是食。” (《大荒南经》)
据考古学的研究, 人类的确经历了一个“不知死活”的蛮荒时代。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人的尸骨都是散乱地瞎扔着的, 有的骨头上还留有被啃食过的痕迹。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并未产生灵魂与冥界的观念, 甚至还像野兽一样地以同伴的身体为食物。只是到了后来, 随着生产力与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 原始人类才逐渐注意到“死”的存在。但是, 他们并不把死亡看作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必然属性, 在他们看来人的死亡完全是由外在的神秘力量所致, 或者是偶然事件中的某种差错所造成的。原始人的这种死亡观从各民族的种种神话传说中可找到确证。
云南独龙族中流传着这样一则神话:“那时, 地上吃的、用的东西都有;人生下来后也不会死, 就像蛇那样长生不老。不知过了多少年代, 还是有人死了。这第一个死的人名叫布和男。消息传开, 人人惊愕, 个个悲伤, 大家都赶来看, 嚷着:‘布和男不该死, 布和男应复活!’四脚蛇也来了, 它对人们说:‘人死了还会有后代, 人死了应该用土埋。大家快去找肉找酒, 对死去的人奠祭一番。’人们听了四脚蛇的话, 急忙拿来了肉和酒, 还找来了一件蓑衣给四脚蛇披上, 让它背上布和男去埋葬。从布和男死了以后, 人就会死了。老一辈人死了, 新一辈又生出来。这是从布和男开始的。人死了以后都举行礼仪式。因为人是用泥巴捏成的, 所以人死了以后也要用土埋。”②
独龙族先民深信人的不死性, 然而无论人活的时间有多么久远, 死亡仍是不可抗拒的, 这是独龙族人首次面对死亡现实, 他们感到陌生、惊恐, 然而他们又以人死了会有后代来肯定了人的不死性 (原始人无可知晓死的无可替代性) 。他们的这种幼稚解释毕竟给他们的惊恐与不安带来了慰藉。
而彝族的神话传说则比独龙族的更胜一畴。彝族在《人类和石头的战争》中说:“天神让石头能长能走, 许愿给人长生不死。由于人类长生不死, 没多长时间就多得在平原地方住不下了, 只好向山上开拓, 凿坏了许多石头。而石头也繁殖很快, 占到了山下。于是, 人和石头战争不断, 两败俱伤, 刚繁荣的大地又荒凉起来。智慧的人在天神面前哭诉石头的残暴, 无智慧的石头一言不语。天神怒斥石头, 并限制石头不准生长, 永远站在原地, 同时, 天神也限制了人的寿命。从此, 石头不能乱动, 人类有生有死。”③
彝族的这则神话与独龙族“布和男”神话的共同点是执着地认定人原本是不会死的。但是死亡毕竟是无可抗拒的, 或迟或早总要到来。当死亡降临之际, 两种民族面对死亡则有着不同的反应, 独龙族面对死亡是那样的陌生和惊愕, 悲伤中不知所措, 怎么也无法接受死的事实。而彝族面对死亡则比独龙族来得坦然:虽然天神许愿人长生不死, 然而石头和人迅速的繁殖占领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为了生存, 人与石头不断地发生战争, 生存矛盾日益扩大, 为了生存无论是石头和人都必需接受天神的公判, 天神限制了人的生存寿命, 也就是说人必须坦然接受死的现实。彝族在接受天神公判时没有独龙族人的那种惊愕与悲伤, 斗争使他们明白了要有生存的空间就必须以死亡作为代价, 生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矛盾, 这为彝族豁达的生死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原本不死的观念在许多的民族和原始部落中都存在, 一种说法认为死亡来到世上是因持有不死口信的使者传错了神的旨意所致。如非洲的霍屯督人中就流传着:月亮的使者兔子给人传口信:“就像我死掉又复活一样, 你们也将死掉并死而复生。”但兔子不知何因却给人带来了相反的口信, 结果人死而不能复生。尔后月亮知道此事却十分生气地打裂了兔子的嘴, 但死亡却无可改变地降临了人间。
在东非的南迪人中流传月亮的信使是条狗, 当狗到达人间后要求与人平等, 要用人的餐具喝牛奶和淡酒, 被人拒绝之后, 它一气之下改口说:“所有人要死掉, 只有月亮才能复生。”
在传达神的口信中, 往往神派的不只是一个信使, 在非洲的祖鲁人神话中说:神派变色龙给人传口信, 让人类永远不死。继而神又改变了主意, 派蜥蜴带去相反的口信, 让人类死去。结果变色龙在路上贪吃贪睡耽误了时间, 让蜥蜴率先到达人类那里传达了神的旨意, 让人死去, 从此人类便有了死亡。
人原本不死还有“蛇蜕皮”的神话传说:人原本是不会死的, 也和蛇一样可以通过蜕皮返老还童。偶然有一次, 一个老太婆与她的孙女到海边洗澡, 老太婆走到没人看见的地方, 脱下她的皮变成了一个少女。然而她的孙女见到她之后便无法相认, 而且孙女十分害怕地要她离开。她很生气, 又回去找到她的旧皮穿上, 这回孙女认识她了, 并对她说:“刚才一位少女到这里来了, 我很害怕, 将她赶走了。”老太婆说:“你不乐意认识我, 好吧, 你会变老, 我则要死去。”从此, 人类就不会蜕皮, 老了就得死去。④这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大洋洲超卜连兹人中收集到的一则神话。这种蛇蜕皮人死的说法在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有不同的流传。
有许多神话解释蛇能通过蜕皮长生不死, 而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好运, 那都是因为人的某种失误所致。如东非许多民族都相信上帝曾召集人和所有动物在一起开会, 问谁愿意蜕皮, 蛇、虾等蜕皮动物就抢先接受这一建议, 而人类的代表却不表态, 结果人失去了长生的机会。还有的神话中说, 上帝本来要将蜕皮长生的本领教给人类, 但由于人的某种过错得罪了神, 神在一怒之下将这个宝贵的权利赐给了蛇类。
由于外因或人的失误造成人必死的神话在我国的彝族中传播的也较多, 如《三兄弟》的神话中讲道:“古时有三兄弟, 老大夺艾学会了鸟语, 老二夺里学会了采药, 获得了一包不死药, 而老三夺勒学会了搓绳, 得到了一根缩地筋。他们凭借各自的本领, 到处搭救遇难的人。途中, 他们救活了一只死去的虎, 还有一只狗和一只鹰。三兄弟领着虎、狗、鹰, 又救活了三姐妹已死去了的爹娘。三姐妹便与三兄弟结了亲。有一天。三兄弟出门去, 三姐妹的爹拿出长生不死药来晒, 不料被太阳、月亮看见了, 各偷走了半包包药。三兄弟将长梯搭上天, 决心要回不死药。虎和狗先一步跳上去了。三兄弟刚要跟着登, 无奈, 梯子脚被蚂蚁啃断, 梯子倒了下去。虎和狗天天咬太阳和月亮, 但太阳和月亮吃了不死药, 咬掉一块长一块, 永远挂在天上。而地上的人和动物从此断了不死药, 不能再起死回生了”。⑤
上述神话故事, 都坚信人类本来是长生不死的, 后来人之所以会死, 都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才造成的结果。他们不是从死者本身来寻求死亡的原因, 而是从死者之外, 从他人、从神、上帝或天使或偶然事件那里寻求人死亡的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原因。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指出:“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 要想象‘自然死亡’实际是不可能的。须知这是一个和其他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独特的观念。”⑥神话中表现出原始初民对死亡的那种恐惧与陌生, 对死亡的顽强否定, 证实了列维·布留尔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 无论在彝族或其他民族的原始初民那里, 人的死亡只具有偶然的性质, 而不具有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性质, 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原始死亡观的另一重要内容 是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彝族的先民始终认为人的生和死都是灵魂的作用, 人生下来灵魂就来到阳世, 若死了, 灵魂就回到祖界。灵魂是永远存在而不会死的存在物。由此 , 他们还把灵魂观推及到他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中去, 以致把一些自然物、自然现象神秘化, 作为有生命、有意志、能操纵一切的对象加以崇拜, 于是出现了种种自然崇拜的习俗。自然崇拜现象, 说明了彝族远古先民的认识水平已经发展到能区分人与非人的界限, 越过了神话时代的混沌圈子, 这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彝族自然崇拜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观念。除了自然现象之外, 彝族先民们对一些生命现象, 如生育、死亡、流血等等也感到十分神秘和困惑, 于是灵魂、鬼神等观念亦随之发展。这些观念人格化以后就构成了彝族原始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为一体的传统信仰。
关于灵魂, 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是这样叙述的: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 本质上是一种气息、薄膜或影子;灵魂是它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命和思想的本原, 它独立地占有它的以前或现在的肉体拥有者的个人意志和意识;它能够离开身体很远, 并且还能突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出现;它往往是不可能和看不见的, 但它能够表现物质力量, 特别是能够作为一个脱离了身体的、与身体在外貌上相象的幻象出现在睡着的或醒着的人们面前, 它能够在这个身体死后继续存在并在人们面前出现;它能够钻进其他人、动物甚至物品的体中, 控制着它们, 在它们里面行动。
无疑灵魂是一种独立的生命体, 哪怕是离开了人的肉体之后, 仍能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幽灵, 这种信仰在世界各国都有, 如在东部美国和加拿大的奥吉瓦人中十分相信灵魂的存在,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死了, 人们还是相信, 他与活着时一样依然有感觉能力, 他的死只是简单地妨碍他同活人以一种他们认知得到的方式交流沟通。他的灵魂完全有意识, 依然具有人的全部渴望和欲求。在我国的《礼记外传》中说:“人之精气曰魂, 形体谓之魄, 合阴阳二气而生也。”在《礼记·郊特牲》中说:“魂气归于天, 形魄归于地。”可见, 我国古人也是将一个有生命的人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肉体 (形魄) , 一部是精神 (魂气) 。
在《搜神后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夫妻二人同寝, 天亮后, 女人先起床出门, 她走后其夫也起来出去了。女人回来时, 见丈夫还在床上熟睡。但过一会儿, 仆人从外面进来对她说:“主人要镜子用。”女人惊奇地说:“他不是在床上睡觉吗?”并将床上的人指给仆人看。仆人也奇怪, 出去把她丈夫叫了回来。夫妇二人大惊, 仔细一看, 床上睡觉的丈夫与外面进来的丈夫一模一样, 于是怀疑是他的灵魂, 不敢惊动他。二人用手轻轻地抚摸床上, 被中那人就冉冉隐于席子里不见了。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人与灵魂的双重存在。
人死之后的灵魂之说, 大多数人都认为人只有一个灵魂, 但彝族则认为人有三魂——即回祖界的魂、守坟地魂与随风飘游或守竹灵的魂。彝人不相信死亡是彻底的绝灭, 因而, 他们的“三魂说”与“祖界”密切相关, 他们认为已故的祖先同样具有三个灵魂, 而且这三个灵魂都会影响和左右子孙后代的祸福兴衰, 因而彝族对祖先的祭祀是极虔诚而又隆重的。
祖先崇拜可以说是彝族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他们深信人是有死后生活的, 为了让祖先或死者生活得更好, 因而彝族的民俗中有着最为频繁多样的祭祖仪式和丧葬仪式。在彝族那里死亡并不被设想成生命的绝对终结。他们对人的不可毁灭性抱有非常确定的信念, 他们执着地相信“死人活着”。
三、原始死亡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是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
既然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 无论是远古的人类还是彝族, 他们都相信人死去的仅仅是肉体, 灵魂则离开了身体到别的地方去了, 究竟这些不死的灵魂到何处去了呢?这个问题成了世界各民族形形色色的冥界神话产生之根源。提到人死之后的去处, 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天堂或地狱, 其实这观念并非中国的土产, 要了解我国民族关于死后世界的观念, 还得从“鬼”说起。
“鬼”字在我国出现很早, 是我国本土的一个古老观念。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鬼”字的形状大约是原始时代巫师祭鬼的装束:下部是一个人形, 上部是一个极其夸张的头部, 似乎是一个带着恐怖面具在跳舞的人。
“鬼”字的本意为“归”, 我国最古老的字书及文献都这样解释:“鬼”, 人所归为鬼。 (《说文解字》) “鬼之言归也。” (《尔雅》) “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 此之谓鬼”。 (礼记·祭仪) “精神离形各归其真, 故谓之鬼。鬼, 归也, 归其真宅。” (《列子·天瑞篇》)
既然“鬼”为“归”, 那么, “鬼”究竟要归往何处呢?当然应该“归”到他本来的地方去了, 这个本来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归纳起来, 比较原始的观念有两个:一是变回氏族图腾原初的状态;一是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 我国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处在氏族部落的历史阶段, 基于这样一种制度, 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超个体灵魂的信念。依照这种信念, 每一个氏族或部落都有一个集体的同质的不死的灵魂, 亦氏族或部落的“守护神”, 如彝、白、土家族等的最高“守护神”为虎神, 苗、瑶、布衣等族的最高“守护神”为龙神。虎神的正统偶像是我国远古的伏羲氏, 龙神的正统偶像是补天的女娲。后来发展为民族之下的地方、村寨、家族、乃至家族都有“守护神”。他们这种超越个体灵魂的信念, 实质上是由原始部落, 氏族中发出来的集体不死的信念。
由于这种集体不死的信念, 云南少数民族几乎都形成了神鬼家族体系, 这个体系中的祖神、社神均为民族的善神、保护神。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祖灵或本族中的英雄、楷模之类受封为神的, 他们受到本民族最亲切和频繁的供祭, 也被赋予保护供主的最重大责任。云南少数民族中无论是藏缅语族、苗瑶语族, 还是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 超越个体灵魂的祖先崇拜是他们原始宗教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和丰富的内容。他们事无巨细, 皆要祈求祖神、社神的保佑与指示 (通过占卜) 。祖神和社神, 从信念逻辑上讲应归入“神鬼家族”, 而这个家族往往是松散, 管理不善, 长幼高低尚未完全分清的“原始神群”。因而在一些民族中, 祖神与社神常常就变成了神系之家的某一分支或某一地区的中心和主宰者, 这种情况在云南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
彝族称祖神为鬼。祭祖称为“做帛”和“送鬼”, 故彝族的毕莫教又被称为“鬼教”。彝族认为不送鬼和不做帛是不文明的行为。他们认为人死之后的鬼魂必须回到祖先居住的本土, 彝族的本土就是云南, 即使是分布在川、黔、桂等地的彝族也是发源于滇, 死后的灵魂必须回云南与祖宗同居。彝族的祖先仲牟由 (觉穆乌或笃慕勿) 是创世纪的人物, 而今滇、川、黔、桂四省有关远古时期洪水的故事都以仲牟由作为他们的共同始祖, 虽然传说带有不同的神秘色彩, 但历史的真实性仍是主要的。
关于仲牟由的原居地, 无论是汉文或彝文的文献记载, 都说是在昆明滇池附近。明正德《云南通志·云南府晋宁州易门县》说:“易门县, 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昔乌蛮酋仲磨由所居之地, 元初立夷门千户所, 至元中改易门县。”《读史方舆纪要》说:“易门旧为乌蛮酋仲磨繇所居地。”易门县南部有座大山叫做黎崖, 亦名蒙低黎岩山。正德《云南志》又说:“蒙低黎岩山在易门县治南五十里, 高插云汉, 下有平谷, 宜牧。”大小凉山的彝文文献记载也说:“当洪水时期, 仲牟由为避洪水即居于此山之上。”《西南彝志·天地产生论》记载说:“天使策耿苴说道:三年前这里 (蒙低黎岩山) 鸟兽都绝迹了, 天师差遣额勺先去江头, 以后转到四方, 挖了十二座大山, 填了八条深谷, 直达江尾, 只留中央一条山脉给仲牟由住在上面。这位老人向仲牟由说, 满了十天十夜以后, 你再往洛尼白去住。哪知道不等到十天十夜, 只满了七天七夜, 仲牟由就牵着马、赶着羊往洛尼白去了。”这是洪水时期, 仲牟由从滇中迁徙到滇东北的一段叙述。这与前述仲牟由的原住地在昆明滇池区域的记载是吻合的。后来由仲牟由因避洪水之患迁到洛尼白。彝族谓山为白, 洛尼白的地望, 在今昆明市的东川区。仲牟由生六子, 后来发展为“六祖部落”。仲牟由实质上正是彝族人部落的超个体灵魂。
彝族的这种原始宗教神话, 是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原始死亡观, 他们相信人死而灵魂不死, 灵魂的归宿就是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这种死亡观不仅是彝族, 在其他民族中也有, 由于历史的变迁, 民族的迁徙, 灵魂要回祖先住地, 往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如在湖南的侗族神话中就流传着, 人死后鬼魂都要回到老祖母住的“雁鹅村”, 但雁鹅村在极远的地方, 要渡过鸟也飞不过去的芦苇塘, 走过一眼望不到的烂泥坑, 爬过99座比蚌壳还陡的大山, 涉过清水河、黑水河、冷水河等, 才能到达。雁鹅村到处是花树, 人们饿了吃仙果, 渴了喝清泉, 成天吹芦笙唱情歌, 游山玩水。亡灵到了雁鹅村后, 能够见到所有亲人, 并都恢复青春和美丽, 连那死去几千年的老祖母, 在这里也是个年轻美丽的姑娘。⑦
正因为返回祖先住地要经过许多艰难险阻, 所以许多民族都有为死者送魂的经文, 彝族的《指路经》正是为死者之灵指路送灵的文献。彝族诵经的毕摩, 其语言具有魔力和灵性, 毕摩能与祖先之灵交流, 祖灵会严格按照毕摩的有声指引一站一站地回归祖界。纳西族也要请“东巴”为死者念《开路经》, 经文中除劝说亡灵前往前祖先住的北方外, 还详细描述送魂的路线。拉祜族的《送魂哀调》也细细指点死者, 如何才能达到祖先居住的“西丹密”, 那地名意即“阴间”。哈尼族为死者颂《米刹威》, 更是明确告诉死者之魂必须走哪一条路, “路的尽头就是打俄地方, 哈尼的祖先正在那里盼望。”“打俄”的所在据传言也是哈尼族的历代祖先阴灵的居住地。他们在另一曲《送魂歌》里干脆把那里称为“阿公阿祖”的大寨。集体不死的信念体现得更为充分。傈僳族送魂的指路词即告诫死者“赶快顺着这条路到你祖先那里去吧, 赶快顺着这条路和他们去团聚吧!”阿昌族的诵经者更是不厌其烦, 在送亡魂经中进一步指明, 哪一条路是哪个民族的归路, 吩咐死者别的民族的路都不能走, 要直往阿昌族祖先那里的路前进。若走岔了道, 不知会去哪家的祖灵, 或许只得去做四处游荡作祟的野鬼。基诺族的《送魂歌》索性为死者开一份地名清单, 以方便其“沿着祖先的路”而去。即使是汉民族也有亡灵“开路”、“过桥”、“起灵”、“发引”、“出殡”、“过七”、“六十日烧船桥”等回归祖灵的仪式。
如此的送魂归宗之路, 本不是由人生现实世界通往灵魂信仰世界的路, 而是由各个民族当今聚居地返回各自祖先原籍的臆想出来的路。它一方面反映了超个体灵魂的不死信念,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传统的。
注释
①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第1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
②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下册第530~53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③、⑤《彝族文化大观》, 第325、326~32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年版。
④马林诺夫斯基《巫求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译, 第111~112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第269页。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⑦何新《诸神的起源》, 第101页。三联书店, 1986年版。
本文来源于《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03期第45-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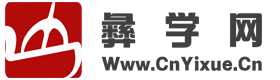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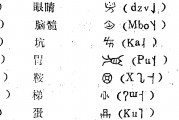







文章评论